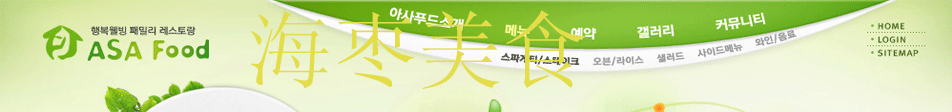|
世界蔣氏宗親研究會 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造成社会的大动荡,人口的大迁徙。南宋末年,“靖康之难”爆发,宋人南迁,在长达百余年的岁月中,偏安江南者约五百万人众,数量之多,规模之大,堪比魏晋南北朝的“衣冠南渡”和唐朝的“安史之乱”。“郁孤台下清江水,中间多少行人泪!西北望长安,可怜无数山,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。江晚正愁余,山深闻鹧鸪。”这首充满了历史泪血的《菩萨蛮》,便是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在逃亡南迁的路上写下的,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通过无数悲凉的诗词流传下来。 元朝时期,蒙古统治者为了施行奴隶制度,将人分为四等:一等为蒙古人,二等为西夏、回回人,三等为辽金统治的汉人,最下等为南宋统治的汉人。对汉人的思想及行为进行严格的管控,稍不如意,便大开杀戒。据元史统计,在最初的九十年时间里,蒙古人杀戮汉人五千多万,再一次造成我国南方各省、省内各地的人口大逃亡。元曲.施惠《幽闺记》第十九出吟唱:“子不能庇父,君无可保臣。宁为太平犬,莫作乱离人…”黎民百姓为了“躲鞑子”,为了活命,为了留下家族的血脉,铤而走险,远投荒野,向陌生的境地,寻找沟渠、溪涧、山岩、洞穴、深谷,来不及思考土地、气候、粮食以及财富等等因素,便在偶然的命运胁迫与驱赶之下,飘零荒野,结缘荒野,让荒野成为家园,成为故乡。 花桥麦元蒋家大屋蒋氏先祖元亮公,既是宋末元初百万大迁徙队伍中的一员,携家眷、带兄弟(元亭公、元亨公、元享公),由祁阳流落衡阳,在原东乡欧东村(现花桥镇欧东村)落籍。 蒋元亮公,祖籍南京,字光儒,号信臣,生于宋淳佑五年(公元年)。自小写诗作赋,熟知音韵,闻名乡里。青年才俊,踌躇满志,取得生员身份后欲参加乡试科考。南宋科考取士要求不仅仅懂得诗赋论,更要懂得治国理民的经义,为的是收复旧山河,统一祖国,重振大宋雄风。元亮公因而刻苦攻读经义策帖,并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与思考。一心救国,志存高远。满腹经纶,文韬武略。元亮公于乡试中举,于会试中贡人,一路过关斩将,文采飞扬,最终于殿试中考取了宋朝最后一批进士及第,被皇上恩准南放祁阳为官,迎来了实现人生抱负的大好时机。 然而,国家的命运决定了个人的命运。由于元军不断进犯,战争持续燃烧,南宋山河破碎,风雨飘摇。一边是前线铁骨铮铮、拚死抗战的忠义之士一批批倒下去,一边是帝都临安忍辱求生、屈膝投降的帝后辅臣们一个个跪下去,南宋灭亡了,一败涂地。年,深怀忠君报国儒家观念,不愿做元朝臣子,33岁的元亮公与全国绝大多数的汉族士子一样,决意弃官绝朝,归隐山野,相忘于江湖。元亮公带着家人在东欧村住了十余年,后继居烟竹塘住了二十余年。漂泊的日子里,耕读教子,诗礼传家。“读书三万卷,仕宦皆束阁。学剑四十年,虏血未染锷。”有谁能懂得元亮公心中未泯的壮志、满腹无奈与悲伤?穿越史册,有谁听见,他噙着失国泪水吟诵的,民族英雄岳飞那气壮山河的宋词《满江红》:“怒发冲冠,凭阑处,潇潇雨歇。抬望眼,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,空悲切。靖康耻,犹未雪;臣子恨,何时灭!驾长车,踏破贺兰山缺,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,收拾旧山河,朝天阙。” 时光荏苒,岁月蹉跎。转眼间,元亮公已由盖世英才变成了须眉皆白的长老。忽一日,于山间习武还家,走在松冈小道上,见烟竹塘又涌入一批难民。虽居山野,人一多,目标就大,烟竹塘也不再安全了。加之蒋氏兄弟此时皆已成家添了子孙,须得分流、择地而居。元亮公打定主意,立即回家与弟弟们相商。当年从欧东搬迁出来,留下二弟元亭一支人脉住在那里,烟竹塘也得留一支,三弟元亨表示愿意留下。四弟元享意欲迁往南乡,元亮公的二子应钜、三子应锦意欲迁往冠市,元亮公则决定与长子应组,到东乡距烟竹塘不远处寻找一个偏僻隐秘的地方。这一次迁徙同样含有远避蒙古人的杀戮和欺凌,但相比过去惊弓之鸟、亡命天涯的状态,又多了一点选择的可能性。应组怀着开创新生活,打造新天地的理想跟随父亲出发了。 因缘际会,一场风雨的洗沐之后,麦元町(现花桥镇),山高水长、烟云幽碧、人迹罕至的红土地,迎来了风尘仆仆的元亮公父子一行。一座高高的山峰,形似一件大大的蓑衣,矗立在麦元町小平原之上,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大衣毛山。不远处,大衣毛山又牵着一座小衣毛山,山形一模一样,仿佛一母所生。元亮公十分中意,蓑衣是江南以棕毛编制的雨具,寓意遮避岁月的风雨。它丰盈的毛发象征子孙昌盛,人寿年丰。大小衣毛山心手相牵,暗合骨肉相连,兄弟和睦,家和万事兴。衣毛山中野鸡啼鸣,野果飘香。衣毛山下,桃花流水,白鹭迁飞,一马平川的田园,可种稻粟,收桑麻,男耕女织,发人发家。他决意在此处开基,如有可能,就在这里世代定居。他激动地想,也许将来国家安定了,蒋家的子孙发达了,在大衣毛山下,修建蒋氏宗祠,供奉蒋氏先祖。在大小衣毛山之间,建造住宅群,形成蒋家大屋。他想起了南朝徐陵的《山斋诗》:“桃源惊往客,鹤峤断来宾。复有风云处,萧条无俗人。”麦元町,实乃乱世避祸,野逸栖身,怡情安魂的理想世界——桃花源。 元顺帝年间,大衣毛山下,最早的蒋家大屋,简陋的元亮公住宅落成了。元亮公率儿女、一家子老少妇孺,从烟竹塘徒步迁徙而来。没有鞭炮,也没有宴席,但有桃花朵朵开放和依稀的鸡鸣犬吠,为蒋氏移居麦元开启了由沧桑归于静宜,从此走向繁华极盛的新纪元。元亮公在堂屋里挥笔写下中华蒋氏通联“三径高风,九侯旧族”,告诉子孙:“三径高风”说的是蒋氏先祖蒋诩,乃西汉廉臣直臣,因不满王莽的专权,辞官隐退故里,在门前竹林开辟三条小路,唯与高逸之士往来,不接浊流,不做脏官。“九侯旧族”说的是蒋氏先祖蒋横(蒋诩的曾孙子),乃东汉时期功勋卓著的大将军,因皇帝刘秀听信奸臣谗言把他治罪诛杀,蒋横九个儿子避难四方。后刘秀悔悟,寻找九子,皆随地封侯,并以王侯之礼葬蒋横,赐碑“显忠”。元亮公告诫子孙:凡蒋氏儿女,无论身处何种时代,何种境地,也不要忘记蒋家人身上高贵的血统,高洁的品性。精忠报国,廉洁为官,诗书耕读,和睦邻里,乃蒋氏传家之本。从今与麦元町结缘,子子孙孙,世世代代,生当作人杰,为蒋氏争光,死亦为鬼雄,要魂归麦元町。麦园町,是故乡。与故土相依,从此不再流浪;与故土相偎,不再远走他乡。 花桥的来历 话说蒋氏始祖元亮公自元顺帝年间定居麦元町之后,他的长子应组公所生景华这一脉,又传思旺、子禄、友政、明炎,至福澄,已是第八代。岁月消逝,人间沧桑。此时,血腥残暴的元朝早已灭亡,日月同辉的明朝也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。早期的嘉靖皇帝英明果断,做了许多大事,他严以驭官,振兴朝纲。宽以治民,减轻赋役。对外抗击倭寇,消除外患。对内崇文尚教,思想活跃。文化科技繁荣,历史上著名的嘉靖中兴由此开创。那正是资本主义在我国萌芽的初期,国家经济活跃,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提高,纺织品、窑瓷等手工业的生产大规模发展,贸易自由,“生意兴隆通四海,财源茂盛达三江”这幅名联便在那时流行祖国大江南北。嘉靖十年(公元年),麦元蒋氏福澄喜得第九代长子,福澄拜谢祖恩,给儿子取了一个谦虚的名,蒋双江,字大时,寄希望蒋家上下生逢其时,从此发家致富,财源满双江。福澄悉心栽培双江,待他在麦元町幼学发蒙,童生毕业后,带上他迁往大城衡州,一边读书,一边学习做纺织品、窑瓷、茶酒的运输贸易。历经三代奋斗,数十年积累,蒋双江富甲一方,登上了花桥历史财富富人榜第一名。正所谓:“纷纷五代乱离间,一旦云开复见天。草木百年新雨露,车书万里旧江山。” 据清嘉庆年间麦元蒋氏第五修族谱重刊考证:“双江公素有大志,不肯拘束如辕下驹。晨夕伺父,左右谨出,纳财巨万。”明史学者研究,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,明嘉靖年间的江南城镇已经出现“近代性质的萌芽”,工商业者的地位提高,影响到城市风气由淳朴到奢靡的转变。那时的衡州古城也毫不例外,崇奢黜俭,十里繁华。明代名著《水浒传》中记诗:“寻常巷陌陈罗绮,几处楼台奏管弦。人乐太平无事日,莺花无限日高眠。”便是将当年市井生活形象嫁接到小说中。在这股活泼、开朗、新鲜的时代气息浇灌之下,奢靡、华丽、安乐的城市氛围包裹之中,年轻的双江公犹能保持“晨夕伺父”的人子孝道,“左右谨出”的事业忠心,实属难能可贵,端的是少年老成,清醒独立,安稳又睿智的英雄人物。双江公看重乡情,谱上刊载,只要麦元町同乡之间有纷争,闹到衡州城来诉讼,他都不辞辛劳,再三劝谕。将双方的吃住全包,劝和之后,还要亲自送到柴埠门河边,安排船只送回。双江公不计得失,淡薄名利,他在衡州城住了近四十年,扶贫济困善举无数,仗义疏财也无数。谱上载有受业生谢海秋对他的感恩、膜拜与颂扬:“高怀出世,流风余韵载道”。明神宗万历十一年(年),51岁的双江公厌倦了衡州城市的浮嚣,梦萦麦元町的野风晴岚,率三子兴国、兴用、兴同,衣锦还乡。衡炎古道转往麦元町的山林深处,马蹄声达达,蒋双江公一路潇洒地吟哦:“试看书林隐处,几多俊逸儒流。虚名薄利不关愁,裁冰及剪雪,谈笑看吴钩。评议前王并后帝,分真伪,占据中州,七雄扰扰乱春秋。兴亡如脆柳,身世类虚舟。见成名无数,图名无数,更有那逃名无数…” 山居是福。回到麦元町最初的时光,双江公在衣毛山下建屋宇,量田地,雇民佣,事桑农,不亦忙乎。五个孙子尚镇、尚钦、尚钜、尚锦、尚锡相继出世,婴孩的啼哭,稚嫩的呼唤,朗朗的书声,欢声笑语,此起彼伏,不亦悦乎。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,竹喧归浣女,莲动下渔舟。”王孙般的日子,不过如此。春芳又歇,似水流年,时光一瞬间又飞到明万历二十三年,双江公六十有四了。忽一日,梦见始祖元亮公清癯的模样,怔忪的面容。醒来思祖先生逢乱世,辗转流落,清贫传家之不易,心内隐痛难安。乃与弟弟大瞿相商,要为蒋家做一件大事。其时蒋家已有百余户子孙,门前大塘与发源于烟泉村的泉圳相连,因修筑不坚固,道路欹侧,人马经常在此跌足。每逢大雨,水性猛烈,更将塘岸决堤,造成水灾,危及族人与周边村民。兄弟俩各出一份,合资修建大塘,环塘皆以坚石垒基础,将泉圳清淤固坝,开源引流,于圳上砌石桥,门前砌石板路。双江公又独资在上游首岸建小桥一座,在江边庄屋门口建步桥一座,形成衣毛山下,半月塘外,泉圳三桥,流经蒋氏百户人家,滋养蒋氏百代子孙,惠及周边百姓群众的风水宝地与生活格局。麦元町边境有一个叫“三角龙潭”的地方,是通安仁、衡山往江西广东方向的必经之地,因溪水勇猛,阻断外来旅客,双江公又捐金独资建设石桥,曰“蒋家桥”。 双江公富居乡里,却从不炫富。相传他有两位发小老友,一个是对江邓家的邓德淑,一个是石坵湾的倪孟虎。邓家与倪家皆是富人家,与蒋家合为明代麦元町三大家族。三大家族也是姻亲关系,邓家的两个女儿分别嫁到蒋家、倪家做儿媳妇,蒋双江的妹妹嫁给倪孟虎为妻。倪家后来迁居相市,明末清初修谱还请了思想家文学家王夫之写序,船山先生追记倪氏家史,谱序中书写了一段有关麦元町的文字佳话,此乃后话。三大家族逢年过节,生辰喜庆,都有来往。那时乡间流行“龙台会”,既每个家族轮流做东,搭台唱戏,宴请宾客,以增进亲情,热闹乡里。因城市生活奢靡,乡下跟着炫富,第一个龙台会,由倪家举办时,倪孟虎公故意将吃饭的桌子摆在不平的地上,等嘉宾坐齐之后,用银锭子塞桌脚。第二个龙台会,由邓家举办,邓德淑公也故意将餐桌摆在不平的地上,等嘉宾坐齐之后,用金锭子塞桌脚。二公的炫富之举引得乡邻尖叫艳羡。第三个龙台会轮到双江公举办时,他也将饭桌摆在不平的地上,等嘉宾坐齐之后,却不拿金银珠宝塞桌脚,而是叫来四个儿孙各执一脚,高抬八仙桌。双江公对众亲说:“在我眼里,比金银还宝贵的,莫过于我的儿孙。”话音一落,举座皆惊,掌声纷纷响起,穿透麦元町悠久的历史时空。 蒋双江公不仅以低调的言行影响着三大家族的崇俭家风,以及麦元町的淳朴民风,而且以开放的思想影响两位朋友,为家乡麦元町做了一件传世伟业。那时南方各省、衡州各地都有了一个“赶集”的习俗,也就是按照农历约定日子,到一个大点的集市去交易物品。南乡定“二五八”,称“赶场”。东乡其他地方定“一四七”,称“赶墟”。无论赶场、赶集,还是赶墟,赶的就是市场,而麦元町没有。麦元町物产丰富,盛产木材和楠竹,豆类、旱烟以及嫩竹纸。麦元町百姓勤劳果敢,渴望富裕的生活,需要一个贸易流通,自由交换的市场。蒋双江公召集老友开会,与邓公、倪公分析了麦元町市场的重要性与美好前景,提出建设计划,邓倪二公深表赞同。于是三人合资,共同开发建设了麦元町历史上第一个市场,名为“墟坪”,就是现在的花桥老街。传说三人在“墟坪”选址环节,出现过分歧。倪孟虎公主张选在桐子坪,位于花桥老街一公里外的山下,蒋邓二公则主张选在麦元江边,现在的位置。意见不统一,争执不下,经山外高人指点,豁然开朗。三公如法炮制,拿来一个量米的筒罐,赴桐子坪量来一筒泥,又从麦元江岸上量来一筒泥,各称出泥巴的重量。泥巴重的,选择放弃,因为喻示着赶集赶不起来。结果是,桐子坪的泥重,麦元江边的泥轻,最终定址麦元江边。又因江水湍急,交通不便,阻断了两岸百姓。双江公慷当以慨,捐金独资,凿石雕花,修建了一座雄伟美丽的“花桥”,寄望麦元町的墟坪市场经济繁荣昌盛,人民生活花开富贵。之后人们来“墟坪”赶集,皆相约“花桥”见面,久而久之,麦元町便更名为花桥。花桥,有花也有桥,随着明万历年间墟坪开埠,花桥美名传扬。 花桥百姓为了感谢蒋公建桥的功德,约定俗成,每年的农历十二月,在花桥桥面上进行交易的摊点商家,主动向蒋家后人交纳落地税。花桥百姓为了纪念蒋双江、邓德淑、倪孟虎三公墟坪开埠的功德,约定俗成,每年中秋在花桥老街搭台唱戏,戏台前搭建三个贵宾观戏台,邀请三公的后代女眷登台看戏,以享祖德浓涎。这两个习俗自明万历年间流传,跨越清朝,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民国时期。掐指一算,近年的岁月光阴。年,弹指一飞间,如今桥不再,街已老,物不是人亦非。住在蒋家大屋一位80高龄的老人家回忆,花桥老街上最后一次搭台唱戏,唱的是昆曲大牌《牡丹亭》,如今依然记得当年盛况,众生营营,熙熙攘攘,千百张笑脸仰头看,台上唱道:“遍青山啼红了杜鹃,那荼蘼外烟丝醉,那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,休凝眸,生生燕语明如剪,听呖呖莺声溜的圆…”观戏台上,衣香鬓影,花桥风情。真个是百年家国身,祖上万丈豪情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