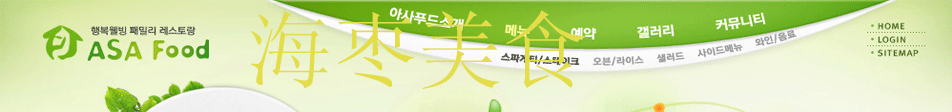|
那些难以忘怀的经历 孔祥国,年4月出生,现任湖南省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副局长、党委委员。年参加工作,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经济学研究员(教授)。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理事;中国企业联合会、中国企业家协会雇主工作委员会委员,湖南省重大决策理论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。湖南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,国家人事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全国人才研究新秀奖获得者。已发表《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》1部、合著6部、主编或参编著作10余部,发表的论文有《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学思考》《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的价值支撑》《培养职业化产业人才大军》《湖南省干部流动情况调查及相关政策问题研究》等。独立或主持完成省部级科研课题3项,参与国家、部省级科研课题11项,完成部省级研究报告28项。累计发表专业著述和学术论文近万字。共有38项成果获得部省级以上奖励,其中全国一等奖8项。 噫吁嚱!蓦然回首,我已迈过人生半个世纪。悠悠岁月,多少陈年故事沉淀在我心间,久久不能忘怀。 我学习了机械制造、经济学、人才学、人力资源管理、行政管理、系统哲学、心理学、中医学等专业知识。在公社、乡镇政府,大型上市公司、大型民营企业、县市省级机关工作过。为中高级科研院所、医院、咨询机构做过力所能及的工作。也为一些大学校报校刊、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做过编审、编辑或记者。 我期待为我的祖国、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。 食不果腹的童年 我的祖籍在山东。清朝时期,高祖考上进士被分到广东当盐道。后因海水上涨,祖上迁移到永州宁远,便在此定居下来。永州,凝聚着我童年成长的所有回忆,永生难忘。 父亲曾在国民党起义部队当兵,转业之后分配到衡阳工作,母亲也在衡阳法院工作。年反右派扩大化,母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。父亲也牵受其中,家里的境况逐渐困难起来。 年4月,母亲在衡阳坐火车回永州宁远的路上,即将临盆,途径冷水滩时生下了我。兄弟四人,我排行第二。 之后,母亲又为我添了两个弟弟。家里的人口渐渐多了起来,加上“右派”斗争的打击,父母要养活四兄弟,实在困难。大伯父只有一女,讲究传宗接代,一心想得一子,希望我过继给他做儿子。父母不忍我们忍受饥寒,便把我过继给大伯父。过继后,伯父也对我非常疼爱。 那一年,我3岁多。 大伯待我如亲子,吃穿用度尽他所能为我提供好的,我也很感谢大伯对我的关爱。当年盛行计划分配粮食。很多家庭食不果腹。我的到来,占了大伯家一份口粮,大伯母心中有所埋怨。当时,我虽只有三岁多,但也稍稍懂些人情世故。为不惹伯母生闷气,每到大伯家饭点,我便偷跑出来闲逛。 有时候,我实在忍不住饥饿,就跑到自家门口,父母家在吃饭,见我饭点回家,母亲和蔼地问我:“你怎么回来了?吃饭了?”我瞧了一眼饭桌,饭菜极少,兄弟们捧着饭碗,张大眼睛望着我,我感受到了他们的饥饿。我低着头,大声朝母亲喊出:“吃了!”然后头也不回的跑开,肚子饿得实在难受。 跑回来的次数多了,母亲起了疑心,后来母亲亲自到大伯家打探情况。这一去,大伯父跟母亲知道了真相,母亲便把我接回了家,大伯父也知道了大伯母对我的不满,还因此吵了架。 年,随着“文革”动乱的扩大,我们全家被迫下放到永州宁远农村,接受教育改造,苦日子更苦了。 这一年,我5岁。 突然下放,从未做过农活的父母感到力不从心,每日农活繁重,还时常开会挨批斗,身体与精神上的折磨相互交织在记忆里,深刻难忘。为此,父母再次把我送回了大伯家。不久,大伯父家也下放农村,食不果腹。对我来说寄人篱下的生活难以忍受。父母无奈又把我接了回来。 家里的白米饭成了稀有物,我的记忆里家里只有年三十晚跟大年初一早上能吃上纯粹的白米饭。平时都是少许米,跟其他充饥食物混合煮着吃,这还是平日较好的情况。 干红薯丝是饱腹的重要食物。记得有一次,家里在竹篾上晒了红薯丝,我特别饿,啥也没想抓起一把往嘴里塞,胡乱一吞,被夹在其中的竹篾片卡住了喉咙,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,疼得我大哭起来。父亲听闻哭声,赶紧跑过来,一瞧,情况不妙,医院取了出来。这样的事还真不少。有一年春末,具体哪一年我记不清了。我到山上放牛,瞧见一片青椒地。当时我太饿了,立马扔下牛,跑去地里摘辣椒吃,辣椒太辣,像吞了滚烫的油汤,喉咙似乎要烧起来了、肚子也痛得厉害。我连忙跑到山泉旁,胡乱吞了几口凉水,缓过辣劲后再接着嚼青椒。辣味太凶猛,我的眼泪、鼻涕一块儿往下流,额头冒出了黄豆般大小的汗珠…… 回家后,我的肚子依然疼痛不已。恰在这时,辣椒地主人跑到我家向母亲告状。母亲一把揪住,把我痛打了一顿。内外皆剧痛,苦日子实在难熬。 饥饿笼罩着我的童年,父亲母亲,是我们的保护伞。有一年,家里种了茄子,刚打完农药,而我们太饿,又没其它东西可吃。母亲将茄子摘下洗净,清水却洗不净农药,为此,母亲先试吃,她吃完后,过了一段时间,确定身体无碍,才允许我跟弟弟们吃。日子虽苦,但在父亲母亲的爱护下,我的童年依旧有美好亲情的熏陶。 多年来,“饥饿”“苦力”“批斗”成了童年最深刻的记忆。从此,我下决心好好读书。我深知,只有读好书,才能吃饱饭。 上学时的乐趣 一路艰苦走来,读书是我最大的渴求与乐趣。吃饱、生存的欲望,促使我在学习的道路上永不停歇。 那时,每日早起后,我要先放牛、刮柴、寻猪草,这些必做“功课”完成后,才匆忙携两个蒸红薯奔到学校上课。小学、初中,都是这样度过的。 在下放的日子,因时常饥饿,父亲渐渐营养不良,在终日的批斗折磨中抑郁成疾。20世纪70年代末期,父亲依然患有别人在60年代初期才可能有的黄肿病。年,父亲最终被折磨死亡。父亲一走,家里的顶梁柱倒了,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四人更加艰难地度日。 这一年,我15岁。 从小学到初中,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。年,我参加中考,同时也报考了中专。我的中考总分排名全县第二。我在县城省直属重点中学宁远一中上学,读了一个月多月高中。中专的录取通知书来了,我和哥哥同时获得了跳农门的机会。可是,当时的生产队,不同意给我卖公粮转户口,说全公社才考上四个,你家就占两个,书都被你家读完了。我无法上学,母亲带着我向驻队的公社革委员会段副主任求情,卖公粮、转户口、上中专才得以实现。 年,母亲被平反,我们一家搬离农村,可惜,当时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。 我考上了郴州农机学校,在此我度过有趣的三年。 读书期间,每月我都能有几块钱生活费,国家会发21斤粮票,我特别饥饿的时候,一餐能吃一斤二两米饭。在这段日子里,我才真正体验到了每日有白米饭的乐趣。虽如此,我还总是感到饥饿。 真正感到吃饱饭的日子,是我后来参加工作的时候了,那时,我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公社工作。 众多学生中,我认为自己算是调皮的,但是,现在的老同学和当时的一些老师,说我太内向、太老实。 我为了填饱肚子,做了不少可笑的事。有一年春天,我跟几个同学跑到后山偷挖竹笋,挖了好几个大竹笋,我们每人抱一个准备跑到老师家,大吃一顿。可巧的是,我的行迹被生产队的人发现了,他找上门跟老师交谈,老师不清楚情况,就带他来找我们。还没等他们进门,我跟同学就做好了防备,一个同学装病,躺在床上,把笋藏到被窝里,我跟另外两个同学就打掩护。在我们的周旋下,生产队干部气馁地走了。我们找老师借灶烧水,用清水胡乱一煮,汤汁都没留下。 本以为会吃得饱饱的,没想到越吃越饿,这没油水的食货,还真不能饱肚子。现在想想,那个时候的自己,也着实生猛有趣。 在学校里,我家的条件当属最差。母亲拉扯着我们兄弟四人。为了帮我们增添几件衣服,有时会买一些便宜的纱自己织,一年到头能买上一件便宜衣服,这算是奢侈了,而我的一些同学就不一样了。 有些家里条件较好的同学,每到饭点,他们就会从包里掏出一包“宝贝”,这是面灰跟豆子混炒的小吃。这时,我就能闻到一阵阵诱惑的香气,馋的我流口水。每遇此景,我只好悄悄走开。 有时,我会每餐少吃一点,慢慢攒一些钱,到周末偶尔也会放纵一下。邀上几个同学买肉、油条吃。有一次,我花了5毛5分钱,买了一大碗面,上面盖了好多杂烩,那次我吃得极香。 还有一次,我花了整整六毛钱,在郴州市的餐馆点了一碗回锅肉,那一会儿真把我吃腻了。虽然有些奢侈,但心里乐极了。 饥饿虽然占据了我大半的时间,但我不曾向它妥协。母亲是我学途中的指路人,她告诫我们,在这个时代,读书才是孩子们有出息的唯一出路。所以,不管生活多么艰苦,母亲从来不肯放弃供我读书。我也一直珍惜上学的每分每秒,在求学的旅程中,把握每分每秒,慢慢向人生的高端攀爬。 在工作中砥砺前行 年夏,我从郴州农机学校毕业。被分配到衡南县云市公社工作,担任公社秘书一职,后任过代副乡长。在公社期间,我拼命工作、学习,得到领导和广大同事的称赞。我于年5月,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。 我任职期间,公社有三个重要任务:一是农业生产管理;二是社会治安;三是抓计划生育。在当时来说,我们的任务相当艰巨。因缴纳农业所得税、公粮和执行计划生育,一些地方的干群关系较为紧张。 有部分干部为完成计划生育任务,用上了强拆强赶手段,冲突事件不少。我产生了许多感想: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工作的顺利开展,无论如何是离不开人民群众支持的。为此,我抱着“政治任务要完成、工作执行讲人性”的原则,深入群众,开展走访谈心工作。 这种温和的处理方式,效果还真不错。村民对我们的好感渐渐提升,也积极努力配合我的工作。 有时,我与几位同事上门查访各家各户任务完成的基本情况,时间稍晚了些,恰巧碰到饭点,乡民们还会热情的招待我们,一桌的菜,青菜、鸡蛋、抓的黄鳝和泥鳅等,这在当时是最好的待遇了。就是蔬菜,豆腐和鸡蛋都是美味了。当然,我也不白吃,总会自己掏腰包,主动给饭钱。 在履行工作职责的同时,我并没有放弃学习。一方面,是自己对学习的渴望;另一方面,还来源于母亲的提醒。年轮一圈又一圈,我的工作渐渐平稳。当时电话较为稀有,写信是联系亲友最快捷的方式。有好几次写信,向母亲汇报工作状况与生活日常,母亲在回信中,都会挑出我的错别字和病句,帮我更正,还时刻提醒我,读书的重要性。 当我静下心细想,母亲的话很有道理,知识是要不断提升的。 自此,我开启了新一轮的学习之旅。除了经常撰写工作材料之外,我还订阅了《语文报》《歌曲》《气功》《卫生报》等报刊,时常阅读,记载好言好句。在有了一定基础后,我时常主动向县广播站投稿,在练笔中,我的文字功底渐渐提升上来,也得了些稿费。 当时机构改革刚刚起步,我因材料写作出色,加上多次在县广播站投稿,引起县领导重视,便在年调入衡南县委老干局,旋即到县委机构改革办工作,工作内容主要集中在整理干部考察材料整理、文字写作等方面。 年,我脱产到衡阳市委党校行政管理专业大专班学习了两年,毕业后仍回衡南县委组织部工作。不久,我任职共青团衡南县委副书记。其间,大部分时间仍在县委组织部、衡阳市委组织部工作。 至今,我仍保留自学习惯,不会打牌、不会跳舞。我还记得,有时团县委举办青年联谊舞会,我只能坐在一旁看别人跳。每次参会,我都较为尴尬。看书,才是我最感兴趣的事。 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,扩大视野,我频繁蹲守图书馆,借阅图书资料,看书看报。后来,我被衡阳市图书馆评为“有效利用图书馆”的典型,先进事迹被做成好几大块模板,在全市各县城乡巡展。 从此,我踏上了漫漫学研路。 漫漫学术研究路 学术研究,是一项严谨的、细致的活儿。于浑浊之中,持清澈;入喧嚣之内,觅静音。 从年始,我被借调到衡阳市委组织部工作。在年,经考试我被正式选调到湖南省人事厅工作。 在省人事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作期间,我在众多部门和岗位工作过。我担任过记者、编辑(《人事与人才)杂志)、做过干部调配、公务员任免考核奖惩、干部培训、人才规划、人才市场管理、社会保险等工作。 岗位繁杂,任务繁重,使我学到了许多知识、增长了多方面的技能。知识的积累,让我不断地深入思考问题,渐渐喜欢上了学术研究。 在20世纪80年代,我的稿费就已经超过工资。当时,我的工资每月只有40多块,稿费就已接近块。 我是中国大陆最早研究人力资本经营、人力资源管理、企业文化等学科的学者之一,我所撰写许多原创文章,被《复旦学报》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》《新华文摘》等刊登、转载。 关于人力资本经营、人力资源管理、企业文化,我有自己的一些看法。我认为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力资源不断突现的历史。21世纪社会面临的基本挑战是人力资源的开发问题,我们要确立新观念,建立新体系,构筑新流程,应用新技术,培养新人才,做出新贡献;要更新经营与管理观念;要改革人才管理体制;要创新用人机制,着力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,扩大人才总量,提升素质和能力,改善结构,提高人才产出和贡献水平;要强化激励;要加强考核;要优化环境;要促进人力资本化。为此,我还撰写了28万字的著作《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》,于年1月由原湖南出版社出版,也因此获评首届国家人事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、湖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、全国人才研究新秀奖。 年,我与几位同志执笔撰写了《湖南省干部流动情况调查及相关政策问题研究》,获中组部重点研究课题一等奖。年,我投中并主持了中共长沙市委、长沙市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开招标重点课题“长沙再就业工程研究”,被评为两项优秀课题之一。 光阴易逝,流年似水。学习不止,工作不怠,锤炼不断。在人生的道路上,我也有过不少过失或错误,但总的来说,问心无愧。我将一如既往,不愧于党和国家,不愧于人民群众,不愧于我所坚守的岗位。 本文转自《名家故事——湖南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忆事》(第3辑) 孔祥国赞赏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