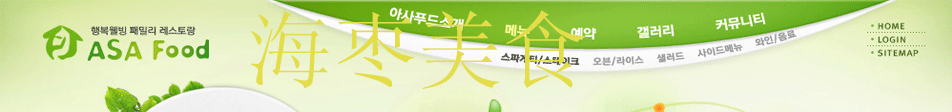|
地名,是一个区域划分的符号,也是一个地方的历史胎记,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情感浓度。平常我们口中所言的故乡,其实是一个被逐渐放大的单元,如果没有走出县,故乡就是我们的出生地;出了外县,故乡就是我们出生的县;跨过省界,故乡就升格成了我们出生的那个省;要是到了国外,故乡就会放大为我们出生的祖国。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动态概念,我原以为故乡是一成不变的。 我的故乡如果要精确到行政村组,细化到军用地图标识的地步,该叫月塘,一个富有诗意的域名。回廊式屋场建在半山腰上,放在城里,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“伴山公馆”了。月塘又有上下之别,我们祖辈居住在半山坡上的这个叫上月塘,山脚下的那个自然叫下月塘,有两口方塘相隔,用一条石板路相连,鸡犬相闻,往来频繁,心与泥土的脉搏一同律动。 父亲健在时,曾向我细述了上月塘的历史,因为族谱并无记载,估计也是代代承袭下来的“故事会”。那块“楚南望族”的匾牌已经作古,无处可寻。取而代之的是由故父撰写的那幅嵌名石刻对联:“月高但任云飞过,塘小却将日映来”。一个教过私塾的老先生看后如是评价:狷介狂傲,立于青峰之上!我读到的却是那一缕乡音、一份乡情、一盏灯影,这大抵就是言为心声的不同意趣罢了。 老家的地名以“塘”命名的居多,如月塘、皂塘、清水塘、排路塘、鲁车塘、羊角塘、日升塘……从地名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世代居此的先民深知无水便无修的农训和逐水而居的道理,十分重视水利设施的兴修。这是繁衍和繁荣的必然需要。 房屋地势较高的,则多以“岭”命名,像文牯岭、牛牯岭、云牯岭……牯岭,也许是一种乡音的叫法,或许也像庐山的“牯岭”一样,是英文COOLDING(凉爽之地)的谐音,我一直以为是某某姓氏加上“家岭”的后缀而作地名的,看来,也经不起推敲。 地势低平的,则以“坪”命名。如:桐梓坪、枫树坪……也有以族居大姓取名的,如唐家、王大屋……还有毫无规律可寻的,像秀屋矶、大岭行、酒铺、绿河池、猛虎跳涧、分手坳…… 不论有着怎样的地名,这都是梦开始的地方。尽管故乡已慢慢看不见炊烟,正在现代化的潮汐中逐渐隐去,徒留一个孤单的身影于大山深处守望,那些地名依然是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,它总是与荣誉不可分割,纵使有一天,我们没有归葬故园,也会归葬在毛边纸的族谱里。 地名,是家乡历史的印记。上月塘,系着我的乡魂。远望可以当归。如果我还没有归来,我一定会把你的名字留下,放在心里晾干,腌制成一道可口的咸菜,在想你的时候,端出来,下酒。 小时候,离开故乡,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是唯一的,那是一条翻山越岭、穿垄过亩的羊肠小道,铺着清一色的石板,留下了光滑的历史履痕。 老家地名好记,八塘,估计在地名考中同名几率也很高。塘作为一个区别地域概念的量词,大抵始于明朝,古《清泉县志》中就有“五里一铺,十里一塘”的记载,如果依照现在的里程来推算,也是较为精准的。老家距离衡州府刚好八十华里,我不得不佩服古人的严谨。 从古衡州府一路蜿蜒西来的这条小路,曾一度称作官马大道,大体相当于今日带G字头的高速公路,“铺”跟服务区的功能相差无几,“伙铺”就是休息区。“塘”则设有驿站,开设了专供往来商贾、驿使歇脚的客栈,其舒适度、服务功能、娱乐功能均高于伙铺,还备有马厩和喂料场。多年前,我在八塘老街那个叫“陶行”(大概是专营陶器的集散地)的旧居前,还看到了三根并立的高大拴马桩,依稀可以映照出当年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来。 八塘是纸牌的故乡,鼎盛时期,老街上做纸牌的作坊有十几家,户户晒纸,家家印字,整条街挂满“贰柒拾”,到处弥漫着桐油的清香。这种家庭合作的生产方式打上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胎印,养就了传统八塘人骨子里的经商意识。当然,也形成了八塘人好赌的个性。在纸牌娱乐方式创新上,八塘人一直走在时代的最“前沿”。桌上有牌有酒,农闲时节,哪家随便一吆喝,三人一围坐,便是一场牌,打得昏天黑地,日月无光。这种劣根性至今也不见明显变易。玩物难免丧志,过去,有打牌贻误农桑的,也有打牌输掉田地家产的,更有甚者,还有因为打牌典当妻儿的,所作所为自是十足的败家子、纨绔子弟了,但那毕竟是特别的个案。凡事皆有利弊,打牌,是一种智力游戏,可健脑,可怡情,亦可养性。印象中的八塘耄耋老人,个个皆是慈眉善目,有金山万丈,玉海千寻之色,而无剑戟森森,鳞甲铮铮之态。看来,娱乐也像一枚硬币的两面,分寸由人,评说由人。 也有从不沾赌的,从这条官马大道走出,到外靠打铁、缝纫为生,我爷爷就是其中的一个,常年在郴州宜章打铁,终老才归。也有往来这条石板路,靠卖脚力谋生,远道广东乐昌一带为盐局商号做挑夫,俗称“挑南盐”,他们离土不离乡,做着艰难的体力营生,总比那些日赌夜嫖的浪荡子活得受人尊敬。 年,民国政府衡阳修建了通往桂林的砂石公路,从现在的泉湖(七塘)裁弯取直,经鸡笼街去往祁东、永州,八塘从此渐渐被边沿化,商家必经之地的优势逐渐动摇,日见式微,衰落凋敝。江山易主后,也不见起色,且愈发一蹶不振,昔日酒肆林立、车马喧嚣之地,终于湮没在山野丛林中,成为偏狭埋名的荒径。 激情的革命年代,八塘曾一度易名“新民”,老百姓用锄头挖出了一条三米宽的砂石公路,拖拉机的突突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,白洋桥水库的修建,则直接切断了官马大道的“龙脉”,青石板在草丛中呻吟,那条充满高贵血统的小道开始长满青苔,渐渐失守、沦陷,淡出了人们的视野,古老的石板也被好事的村民一块块用铁锨翻起,成了修葺猪圈牛栏的上佳建筑材料。 近些年,新农村运动的“村村通”工程,渐次打造了宽阔平整的回乡之路,新湘桂线的动车以公里的时速从家门口呼啸而过,老家空巢的洋房也越建越多,逢年过节,我们开始堵在了回乡的路上.........这一切,并没有带给我多少惊奇,相反,我感觉故土陷入因整容而毁容的时代怪圈,看不到那条记忆中的石板路,身后的脚印、村子,梦里的八塘,连同乡愁,都渐行渐远,变得模糊不清。 家乡属于典型的山地丘陵地貌,有山不高,有壑不深,有水不阔,有田不广。植被倒是葱茏葳蕤,一年四季,郁郁青青。“唐家”左侧有峰兀立,呼作“将军岭”,得名由来已无从考证。如果历史可以大胆臆测,我想,应该是在某个朝代,某个镇守边关有功的将军,受到朝廷册封,赐良田美宅定居于斯,仙化后厝柩在那个山坡,所以命名“将军岭”。当然这种缺乏史料记载的臆测难以接近历史真相,近乎戏说。 我一直不太明白离家不过数百米之隔的那个中二型水库缘何取名“白洋桥”?古人定义“桥,为水梁也”,没有取名白洋町,盖因兴修大坝时架起了一座小桥吧。查阅《舒氏三修家乘》,里面有关于“白洋町”的详尽记载,甚至连田亩主人都被记录下来。町为田界、田地之意,白洋町用农村熟悉的语境表述,算是个大的垄口子了,在一个丘陵山地为主的乡村,是很难觅到这么一处集中连片的沃土良田,且地势开阔,光照水源也十分充足,怪不得历代被朝廷看重,累受册封,以奖军功。 白洋町修建水库约有六十年的历史了,那里的每一道波纹都刻有父辈的记忆。父亲是当年负责工程建设的指挥长,母亲在大冬天随同三千余名建设者一起喊着劳动号子,挑土打夯,那些珍贵的汗水就是注入白洋桥水库的第一股碧流。用石子堆砌的“农业学大寨”那五个十米见方的遒劲大字经不起风化的煎熬、皴裂的沧桑,早已不见踪影、魂宿大泽。心态急躁的人们急于向水索取,一年一捕,这些年再也看不到儿时比己身还高的青鱼、雄鱼了。水养万物,作为周边数千亩农田的灌溉水源,如果没有白洋桥水库,也许,这一方水土、人文,还有以谷稻为食的乡民,都将枯萎,成为无家可归的乞丐。 这一湖清波,是丰收的闹铃,是故土的命脉,是窖藏的老酒。她唤醒季节,催生希望,一旦拔了塞,奔流中便溢满陈年的芬芳。 将军岭、白洋桥,一山一水,不再单纯是一张故土的地域名片,而且可以烛照一个时代的脸面。我深爱这片汪野,这方灵动的山水值得我带着余年,抱朴还乡,筑庐为居,托体植骨。 乡音、方言,从来就属于故土的一部分。它流淌着血脉的亲情,给人以强烈的自身地域文化认同感。故乡,是一个人的根。而乡音,便是代表这条根的最深符号,也是一方水土、一方文化的最深烙印。当下的城市,已经成为南腔北调的汇集之地,所有的口音,都透露出投奔者的个人背景。于是,乡音成为投奔者们极力摆脱的对象。 我的家乡泉湖,地接衡祁,使用的方言属于南乡语系(大衡阳传统上有东乡、西乡、南乡、北乡之分),我在那生活时间虽很短,但还是从父母身上承袭了一口地道的乡音。这种地理表征和情感的纽带,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的语言习惯,它有着普通话难以比拟的亲和力和凝聚力,以其鲜活自然传达出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性情与趣味。一个地域的方言无疑是一个地域最形象、最真实的一种展示。年岁愈长,感觉愈深。 前些日子,从好友处偶得一本李伯陶(---9)先生的《野语文说》,读之,爱不释卷。先生籍衡阳县大安乡,毕生传道衡阳县五中。多年执着于俗语的研究和整理,以衡阳方言为母本,涉猎广泛,尽搜野语村言,以雅释俗,成之天然,堪称一部衡阳地方方言百科全书。西乡与南乡原本一家,五十年代才析为衡南、衡阳,由于语言同源,读先生的文集,仿佛是在听一段乡音叙说的故事。尽管伯陶先生墓木已拱,但先生为留住这些“逐渐消失的声音”所付出的辛劳,是对文化多样性保护工程的莫大贡献。 语言是一种兼具工具属性和文化属性的特殊产物,在工具的标准和文化的多元之间,需要一种善意的平衡。所以,我们大可不必从心理上排斥方言俚语的存在。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,有着特定的精准表达,它就是乡音、方言。在此不妨列举一些,练舌养耳。在我们老家,年长者常用“老人不翻古,后生失了谱”来说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;“鳙鱼头,草鱼尾,鲢鱼肚皮鲤鱼嘴”,这是乡村美食家的箴言;“想赚畜生钱,要和畜生眠”,道出了养殖业的真谛;“买田看塘,讨亲看娘”,言明办事要察本;“只有锅子煮白米,冇得锅子煮文章”,强调了务农为本;“上磨肩膀下磨脚”,言农桑、负重远行之苦;“口头打官腔,屋里擂斋汤”,喻人死要面子;“屋檐搭屋角”,谓近邻之亲;“背蓑衣打火”,告诫不要惹火烧身;“挖堪寻蛇打”,言无聊而自招危殆;“告花子卵,夹(烤意)不得火”,形象比喻秉性贫贱,富贵不得;“稿菅人,三日不打起灰尘”,以此告诫孩童不严管则放肆生事;“左拳不打,右拳不来”,说明于事于人付出而复补有时………… 在我的记忆里,一声“卖豆腐”的叫卖,至今还荡着悠悠的乡愁。乡音质朴、直率,是一幅水墨山水画,虽没有色彩但底蕴深厚。乡音委婉流畅、回味无穷,是一首诗,一首山水田园诗,有朝阳,有余晖,有一种无法释放的情绪,无论走多远,都始终牵绊着乡愁。尽管,乡土不过方圆几平方公里,乡民,不过几百户人家,但哪怕喝一口井水,从味蕾到喉哽再到心间,都带着清凉的丝丝甜蜜,滋润着全身的每一个细胞。 “未老莫还乡,还乡须断肠”。这些独特的乡村语言是故土鲜活的“族谱”、“史册”,跳动着我们生生不息的脉搏,是故土的标志,乡情的寄托,乡恋的梦境。无论我在怎样的年岁归来,我都不会忘记这些朴拙、最靠近田园样本的生动语言,它是我心中永远的梵音,也是无法取缔的乡村精神记忆。 (本文节选自我的原创乡土系列文学《故土杂记》) 作者简介: 余波,籍衡南泉湖,现供职于衡南某机关。著文写字虽不为稻粱谋,然大半辈子以五谷为业。勤于稼穑,为耕者谋利,为食者造福。信奉以儒做人,以道养生,以禅养心,以墨尽责。闲暇时光,常透过笔下的每一个文字看社会,看风景,看世态;在定格的每一帧图片里见自己,见天地,见众生! 赞赏 人赞赏 德国强力白蚀消儿童白癜风的注意事项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