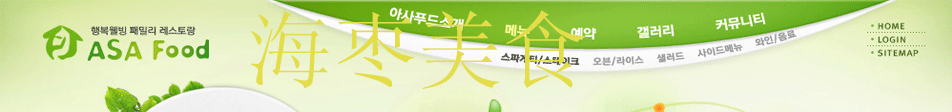|
点击题目下方耒阳快讯 让耒阳成为我们的永远骄傲! 水是生命之源。人类的起源、生存、延续都离不开水的滋养。自古以来,人类就懂得择水而居,沿河湖而居的生存方式。 耒水,是湘江最长的支流,春秋战国时期称雷水,汉朝之后称耒水,现代称浙水,源出湖南省汝城县耒山,到程江口称东江,东江与程江汇合于永兴而称便江,出永兴后称耒水,西北流,至衡阳市东耒河口入湘江,长千米,流域面积平方千米。为湘江流域各支流之冠。 在水运逐渐发达的时代,湘江支流的耒水,流经在耒阳境内,从南到北,形成五大繁华口岸:大河滩,灶市口,肥江口,新市街,小江口。(小江口属于耒阳和衡南交界处) 过去如果有人说:“我上到大河滩,下到新市街。”言外之意是:我哪个口岸没走过?这是自诩为见过世面的。 耒水,在出永兴县而进入耒阳境内之间,由于地势平缓,河床宽阔,水流由急促而舒缓,水域宽阔,最适合停泊大型船只,这就是我们耒阳著名大河滩。据说,在光绪年间,以大河滩为中心,形成一个商业圈,这个商业圈以上堡古街、黄泥岗、清水铺为中心,形成一个大型的繁华的口岸,俗称“三个半口岸”。 我们走进清水铺,在当地村主任的带领下,找到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,向我们讲述清水铺当年的繁华景象。 据清朝光绪年间的《耒阳县志》有记载:“清水铺,县南五十里。”说明清水铺,作为一条商业古街,最迟起源于光绪年间。 遥想当年,在耒阳南部一隅,有一个静谧的小村落,倚枕湘江水系——耒水,住户两百来户,人流不多不少,却是一个繁华的商贸之地。它南临耒河水,北坐高山,高山瀑布飞流而下。宋朝诗人郭印有诗为证: 飞泉溅石落寒岩,更喜朝来一雨添。 疑是玉姝离洞户,故垂千尺水晶帘。 我推测,清水铺名字的由来,或许就是因为北面高山的清泉而来。 我们来到一个老人家里,正遇到老人的儿子儿媳妇在蒸糯米,酿醪糟。清水铺的“豆腐”和“胡子酒”闻名远近。不知是因为清水铺的水质好还是因为清水铺的制作方法别致,也不得而知。 我们静静地观看他们酿制醪糟的过程。蒸好的糯米自然凉却,当糯米与人体体温差不多的时候,把糯米倒进陶缸里,在糯米上撒上特制的酒曲,加冷却的开水和匀,一人慢慢倒水,一人不停地用双手就着凉水搅拌,把酒曲渗透到糯米里,然后,用手掌把糯米慢慢扫平整,再在糯米中间,挖出一个拳头大的小孔,以便糯米发酵以后,酒液慢慢渗到中央。然后盖上簸箕,把陶缸放到铺好棉絮的箩筐里,再把四周的棉絮包上整个陶缸,一个对日以后,开包,酒香四溢,就是我们当地的特色食品——醪糟。醪糟,我们也叫“胡子酒”。 让人不解的是,为什么不直接叫糯米酒,而是叫胡子酒。酒之名称从何而来?我想,这或许与一段历史有关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庞统传》记载:“先主领荆州,统以从事守耒阳令,在县不治,免官。”作为“南州士之冠冕”的庞统,认为小小一个县令是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的,于是“在县不治”。传说,刘备听说后派张飞到耒阳来督察,庞统的下属担心猛张飞一时冲动造成不可收拾之后果,待其一到耒阳即以此酒为之饮。此酒度数低,极易入口,但后劲大,猛张飞一顿狂饮海喝,大醉三日不醒。庞统在短短三日之中,竟将积压三年的案件文牍全部处理完毕。此酒名声遂不胫而走。酒亦因猛张飞之髯虬胡子,名为胡子酒,或者,因为此酒迷糊了猛张飞三日,而称为“糊子酒”,亦未可知。 但是,清水铺如果仅仅有豆腐和胡子酒,不足以形成一条商业街道。从光绪年间一直到民国初期,清水铺,曾经是耒阳南部地区最繁华的商贸之地之一。 清水铺,隶属黄市镇管辖,黄市、上堡一带,是个风水宝地,物产丰富。山峰连绵,楠竹成海,绿树成荫,古树林立。而蕴藏在深山之下有煤炭以及丰富的铁、锰、铜、锌以及水晶,还蕴藏着亚洲稀有的高岭土等矿物质,地壳运动形成的版块,又是大理石和麻石的最佳最丰富的产地;加之耒阳河水流经这里,形成一个宽阔的地带,适宜泊船。所以,这里是物流的聚散地,也是一个自由贸易口岸。 这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,是清水铺之所以成为商业街的前提。据说,当年这条商业街,从南到北,约有三里之长,有上街、中街、下街之分。公元一九四七年农历六月初十,确定正式开圩,于是凡是逢五、逢十这两个日子,就是赶圩的日子。这约定俗成的赶圩之日,周围几个乡镇村民,挑着自家的出产:竹笋、红薯、豆子、板栗,或者自己编织的竹篓、竹篮、竹筛,还有时新蔬菜、鲜活的河鱼、肥壮的鸡鸭来到清水铺,换取自家需要的日常用品,圩场非常热闹。交易完毕了,来到茶馆酒肆或米粉店,喝一碗胡子酒或土茶,吃一碗现榨米粉,带着酒意,满意而归。 据当地老人讲述,清水铺在最繁华的时候,临街每户都是商铺,草药店、杂货店、布匹店、胡子酒铺、豆腐作坊、米粉店、茶馆酒肆、盐铺当铺,甚至在街尾还有“花屋”。“花屋”,是富家公子寻欢作乐的场所,也是脚夫寻花问柳的去处。 脚夫,也就是“挑夫”,在当时,也是清水铺一道风景。他们家住深山,农闲的时候,就来到清水铺,帮助船家挑米挑煤上船,然后又从船上挑沙挑盐下船,或者搬运楠竹、木材。“挑夫”,就是水运时代的搬运工。 随着时代的变迁,社会的发展,陆地交通的发展,许多繁华的码头、驿站、驿道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,清水铺,也再不见当年的繁华。如今,走在清水铺,“三元堂药材”、“长喜纸码店”、“福盛布匹店”,这些古老的店铺,仅存于斑驳的木牌里,青石板路上铜钱纹饰的麻石下水口,在历经风霜以后,依然清晰;用于捣碎药材的石臼,安然于破败的店铺前,而那童叟无欺复称之物——石斗,静立在杂草里,似乎在向世人不停地诉说自己当年的铁面无私。 沧桑岁月,一言不发。任凭历史的风烟吹过,清水铺,始终以自己的特色安于耒水之滨。如今,商业的繁华虽然不复再见,可是,我却在清水铺,找到了一种宁静与安详。 我们在村主任带领下,走进清水铺尾街的西北角,在古树旁,一座不算豪华的寺庙“三宝寺”肃静在山脚下。这是当年的清水铺的“宝王庙”、“农王庙”、“杨四庙”三庙神仙汇合之庙。当地老百姓把来路不同的神仙,恭请到一处寺庙安身,也印证当地人们奉行有容乃大、和谐为福的理念。 “三宝寺”的后面,虽然有山,但并不高大,也不见清泉飞流,站在高处,只见飞鸟欢歌而过,只见耒水缓缓北流;走在古街里,也不见商铺林立,商贩吆喝,只见三三两两的老人,坐在屋檐下、阴凉处,纳凉、闲谈,几个抱着小孩的妇女,带着奇异的眼光打量着从外面走进村里的陌生人。当得知我们是为清水铺采风而来,她们很兴奋,也很热情,招呼着这些陌生人进屋喝茶水。正值礼拜日,放学在家的孩子,在古街里,或骑着单车飞驰而过,或坐在屋檐的阶梯上,窃窃私语。 藤蔓爬过荒芜的古园,小草点缀在古宅零乱的瓦楞上,大母鸡迈着八字步,晃悠悠地在屋前“咯咯——咯咯”地唱着悠闲的歌,小黄狗懒洋洋地趴在店铺的门槛边,闭目养神,似乎在做着一场美梦。散落在断壁残垣处石臼、石墩,在无声地诉说当年的繁华和岁月的沧桑。而忽而落地觅食,忽而立在电线杆上叽叽喳喳的小鸟,任凭外人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它们,它们似乎知晓:你们不过是匆匆过客,我们才是这里的长住客。这里的山山水水,也是小鸟的天堂。 古街口的那家酒店,生意兴隆,游人都是冲着清水铺的“豆腐”和“胡子酒”而来。悬坐在村口麻石上的几个顽童,在我们摄影师抓拍着他们的神韵以后,居然顽皮地讨价还价,索要奖励;那几个年轻的母亲,怀抱着婴儿,或喂奶,或闲聊。看见我们一路行人,热情招呼:“进屋喝茶呀!” 走过繁华,是境界。如今,清水铺的人们,守着古街,顺着农时,循着古习,过着一种安然知足逍遥而居的生活,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桃园呢?(责任编辑:李辉) 文/郑菊芳杨敬忠 爆料采用即奖10-元 爆料 投稿 合作 免责声明:本平台按各网站网帖推送的任何图文言论不代表本平台立场,文责由原发帖人自负!以上内容源自网络,版权归原作所有,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,请联系本平台我们处理!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 |